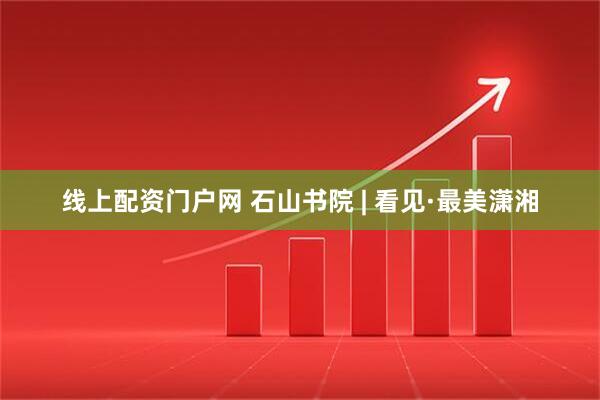
在中国书院中,石山书院年岁最高。公元498年,南齐司空张岊辞官栖隐攸州麒麟山,辟寓所30间,另修书院一座,因书院坐落于麒麟山分脉光石山下(现为石山)而得名。
石山书院。
(一)
南北朝乃民族融合交汇期,刀枪出鞘,战祸横生,儒家难持天下清安,朝堂纷纷扰扰,时有焦虑。齐明帝萧鸾竭尽心力,得一时太平。
其驾崩后,东昏侯萧宝卷嗣位,内不修礼制,外不听臣谏,纵恣秽行。朝野躁动,动荡不安,不少性情高远之士,远离朝堂,避隐山林,过起了悠哉游哉的日子,张司空亦如此。
展开剩余81%南北朝时,司空、太尉、司徒并列“三公”,司空一职虽显实权不济,但地位显赫,不容小觑。张司空见自己的主子萧宝卷如此昏庸。仰头兴叹:“正直不任,而耽女色,齐国将亡矣。”
遂具奏阙下,挂冠东门请休。诏下不许,乃曰:“君不任臣,臣今老矣,人生所贵者,在乎适意耳。”诏乃许,倾朝饯送。于是,张司空携家去阙,思乐林泉,一路寻访,先落脚衡阳,慕名而来者甚众,不利清修,居数日,随山情水意,辗转来到光石山。
唐天宝年间潭州刺史苏师道来攸州赈灾,悉闻张岊之事,写下《司空山记》,其中曰:“司空宅在山之西,去观一十里。今殿宇有像,坛井基图,宛然在焉。宅左有光石山书院,故基尚存。”第一次提及石山书院。
同时,提及书院以北一里有惠光寺,十里之外有菩提寺,又去三十五里,有隐真岩,是司空炼药时栖止之地,还有荷池、药池等,并作了水清如鉴,芳华甚异,犹有药香徐涌等记述。
张司空在此隐逸潜修,教化乡邻,治病助人,名震千里。平时,采药炼丹,浸泡仙池,掬饮灵泉,留下了不少奇踪异迹。如今,麒麟山容颜未改,隐真岩、药池犹在。只是“故人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,难免让人心生感慨。
苏师道所述司空山,文辞隽永,意象丛生,不仅道出了书院源起转承,还对张司空炼丹修道,怡养荷莲着点睛之笔,言词散淡,巧织时空。《司空山记》中的述异之事大多源自《述异记》。其他写景叙事,多为亲历之言,细品深耕,可窥不少心机。
到了五代十国时,修道之人陆蟾慕名前来,留有《司空山闻子规》诗:“后夜入清明,游人何处听。花残斑竹庙,雨歇砚山亭。树罅月欲落,窗间酒正醒。众禽方在梦,谁念尔劳形。”其诗空灵惆怅,吐露了陆蟾内心的愁绪。月光沮丧,鸟儿酣睡,自身疲顿,难入清安之境,表达了陆蟾对张司空隐逸清修,不碍凡尘的羡慕之情。
《文史博览·人物》2025年第9期 《石山书院》
(二)
石山书院的第一块匾额,乃南宋易祓所书。易祓为宁乡人,南宋淳熙年间状元,官至礼部尚书。循张司空足迹造访到此,并留下司空山石山书院墨宝,将苏师道所提及的石山书院挂上了司空山的门楣,延承了司空山文脉,也拉远了湖湘书院的风檐。
有人说,石山书院比官方倡修的书院早了两百多年,可谓天下第一书院。此种说辞有其道理,但仔细考究,又颇存忐忑。史料记载,唐代官方书院共有两所,为唐玄宗期间创办的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,也可说成是一所,因为集贤书院是由丽正书院更名得来。
那时,官方书院并非授业解惑的课堂,而是朝廷整理修撰典籍的地方,类似现在的档案馆,朝廷的学堂称为太学。太学为皇权服务,非皇亲国戚家的孩子,上不了檐阶。
既然官方书院和民间书院寓指不同,岂可并置一起,用以佐证书院文隽先后。何况,张岊栖隐之所,在最早的《述异记》中,亦未出现书院一词。
张岊作为退隐之士,利用自己当官时积攒的银两、声威、学识、人脉,创办讲习之所,教化乡邻,福祉一方,有理有据,合乎常理,未有歧义。
元、明期间,石山书院遭毁损,明崇祯年间得以修复,并留有明代文人林奇所写的《石山书院记》。清初,石山书院再遭劫难。康熙五十年(1711),天目禅师在书院旧址建大觉寺,当地士子以寺院当书院,勤耕苦读。
至此,石山书院渐行渐远,消隐于晨钟暮鼓中。清人廖梦麟曾在此就读,其有诗云:“虚灯闻落叶,纤月下残钟。读到忘言处,浮生失所从。”儒子之怀,空灵之境,若隐若现。
古代,攸县的名头不小。张岊辞官后,不回广东清河的祖居,而是千里跋涉,归隐于麒麟山,自当有其道理。石山书院作为中国民间最早的书院,沉甸甸的文脉印痕,比湖湘书院史上名头最大的岳麓书院还早了将近300年。
不知张司空创立的书院,是否以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为教义,张岊本人师承哪家学理,留下过怎样的著述,无从可考。有人说其盘坐学子之中,举木铎领唱诸子贤文,也有人说其道行高深,精于炼丹制药,其去世后,乘云驾鹤而去,不仅留下了石山书院,还留下了阳升观。
(三)
新修的石山书院居攸县文化园中轴线北端,占地1500平方米,南北朝向,前后门楼气宇相道,不分前后。整个布局为回字形结构,园林建式,宫廷气派,中轴上有大殿、前殿、前后门楼、两侧为钟鼓楼、厢房,各显檐廊,既有书院之幽,又显山寺之风、古阁之韵。
南面门楼,远眺碧水一湾,柳枝摇曳,拱桥如月,与湖上风光连为一体。北面门楼,近临城区内环路,与城市繁华接肘连襟,高远之怀不避世俗之喧,可谓盛世华章。
如此巧妙布局,匠心非浅,文心独具。南北朝(南齐)时,民间书院尚没有祭孔、授业、藏书一说。张岊做过朝廷司空,又是一个修道之人。其对育人栖所的理解,肯定和后来的考量不一样。
恢复的石山书院,采用园林制式,宫廷风格,不亏礼尊,崇尚实用,美哉妙哉。
最让人欣慰的是,新修的书院兼顾了唐以后书院的配置,还兼顾了现代书院的功能,借此褒扬了攸县千年风月,颇显厚重之端庄。
从书院正门拾级而上,前廷敞豁,梁顶高矗,肃静之中文盈气满。进入大成殿,里面奉有先师孔子之像,还有“论语”的精雕木刻,以示祭孔、尊师、尚学。另有讲学堂,藏书阁,功能齐备,可延教化之功。
攸县山水清幽,人文鼎盛。石山书院之后,陆续创办的书院超过20所。从隋唐到清末,攸县士人中共有进士85名、举人248名,还有多位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有的书院墙砖基脚犹在,有的和现代学堂融入一起,仍在教书育人。
走近石山书院,重拾中国民间第一书院文隽,是对张司空最好的惦记。近观司空山清幽之境,梳理湖湘书院源起,重塑司空山文脉。一路走来,心旌荡漾,有如林泉相叙,佩环相鸣,古韵空灵,不绝于怀。
文 | 骆志平线上配资门户网
发布于:湖南省亿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